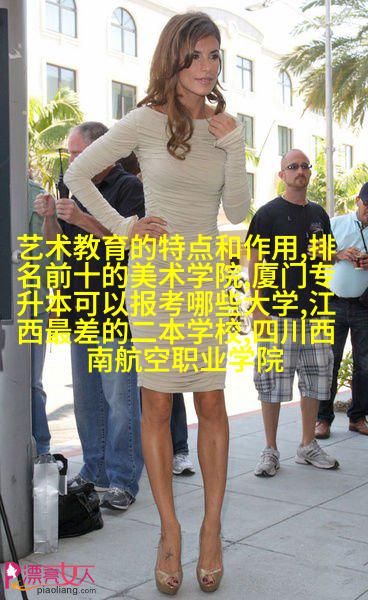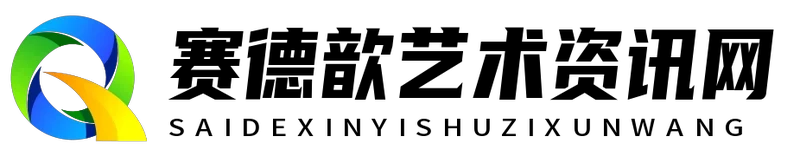周阳明:我看见了
艺术家周阳明在画廊空间的首次个展「我看见了」于2024年7月26日在白盒子艺术馆隆重开幕。展览由栗宪庭担任学术主持,徐薇担任策展人,展出艺术家最新绘画作品20余件。本次展览持续至2024年9月16日。


我看到了
文/徐薇
限定的,完美的,可掌握,可利用。
将万物打磨成以上标准,即可感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与安全感。包括孩子、关系、艺术,以及“”。这是平滑无瑕,清晰可靠的确定性,如个人简介中的标签。我们在制造与收集这些标签的过程中建构生命,标签的光鲜与否体现着生命质量。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吗?
平滑的标签为提升系统的运行效率而生,而生命本不应是困于系统中的游戏玩家,生命是“如其所是”的自然生长过程,生长中充满了不平滑的迂回与踯躅;也绝非肯定或否定的单一答案,是允许其“如其所是”地展开,展开的过程伴随混沌与隐秘。


我们往往渴望一种解说的方式,一门学问可以答疑解惑,但事实上“我们永远都不要有这样的想法,认为一种艺术形式的语言是可以与另一种艺术形式的语言进行互换的。”正如罗斯科所言,是不可化约的,不可能通过切分成平滑的局部来认知,我们是否有可能通过阅读描述罗斯科的文字来体验作品的悲悯?通过背诵糖的分子式来理解何为甜?无论模块化的拆分多么精巧、正确,也无法澄清的全貌。而真正看到的那一刻,是抽象作用于感官时的具体,是对不可名状物的肉身体验。


澄清如其所是,正是这个展览的工作。艺术家周阳明抛弃了那个如乐高模块一样,可拆可组的浅表世界,那么,如何以艺术获得救赎?将自我掷向虚无的解构无法救赎,虚假亢进的竞争也无法救赎,他选择了第三条通往救赎的道路——建构内在的无限性。在清理完浅表的标签后,让与强求的意志都隐没,在消除目标的层层构建之中,将内在频率推至极限,消除与构建在同时发生,遮蔽与,也在同时呈现。
你将在何种视角下看到被澄清的?
1,谦卑的主权
这是一张没有“念头”的绘画。
任何念头,都可能被利用而走向偏离。为何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如此推崇以抽象表现主义为代表的先锋艺术,因为“从法西斯主义的观点来看,先锋艺术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因为它们太富有批判性,而是因为它们太‘清白’,以至于无法有效地在其中注入宣传煽动的内容。”如果在1939年格林伯格笔下的“清白”意味着从极权到的意志回归,那么在近100年后的今天,“清白”是从自由的情绪性表达,转向超越个体情绪的持续概括。但推动概括的并不是出于艺术史的自觉,而是良知的自觉:“艺术不是一场崇高的降落,从无限降落到身体和性欲的有限的不幸,而是通过物质减法的有限手段生产无穷无尽的主体级数群。”正如阿兰.巴迪欧所言,个体化的情绪偏离不是艺术的目的,而自觉地将手段进行减少时,主体才有可能走向无限,走向救赎。
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让我们回到周阳明的画面,这是去中心化后的全然臣服,没有一个笔触是煽情故事中的演员,没有极权,没有主宰,但每一笔已臣服于安住之中。因为艺术家自觉地做到了两点:清除绘画作为商品意识的表现性、还原每个笔触作为主体的表现性。但笔触的单体表现意识并不是彼此割裂与分离的,这种“浑然不知”又“保持全知”的训练,令人想起庖丁解牛中的游刃,它并不寻求主宰,而是一边集中意志,一边顺应力量场,气韵在其中流动,一种美妙的效果涌现出来。
不寻求主宰,事实上才能达到主宰的效果,因为谦卑是“空性”的,而空性才是常驻于万物的永恒主权。如《庄子·至乐篇》中庄子和骷髅的对话,骷髅说“从然以天地为春秋”,当变为骷髅后,可能性才再次得到了舒展。通过谦卑地接纳死亡,事物消解自身,获得了超越的可能。谦卑从不虚无,只是消除了执着的边界,坚韧而安静地,依从规律运行。
这些细密的笔触灭尽了念头,正在试图将主权归还于观者的观感之中。
2,“一”的救赎
这是一张在修复坚固之物的绘画。
罗斯科在参观雅典时期的神庙遗址时,当地人问他是不是来画神庙的,罗斯科回答:“在我不知道这座神庙之前,我一直在画希腊神庙。”所以,伴随着20世纪后现代主构之路的持续推进,罗斯科的也成为了必然宿命。当坚固的“一”成为了变幻的无限,当万物相连的宇宙成为了满足需求的巨大超市,如汉娜.阿伦特对技艺者的描述:“把整个自然看成一张巨大的网络,从中裁剪出想要重新缝制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罗斯科所象征的与神庙作用相同的艺术,被剥夺了内在的坚固价值,徒留波动的交易价码。
当一个人,一个艺术家对这种剥夺感深恶痛绝时,在向外抵抗与向内自戕之外,是否还有第三种夺回价值的可能?尼采的“永恒回归”理论曾试图让人徒手掌握这一极限之力——“视辛劳为最大喜悦者,竭力辛劳吧!视休憩为最高享受者,尽情休憩吧!最爱服从、遵依、追随者,尽管顺从吧!重点是清楚地知道自己要什么,且无论如何也都不退让!这其中就有永恒!”对于尼采来说,完整地感受当下,不以外界反应来转移意志,便与永恒没有区别。但这种“永恒”与善恶无关,只与纯粹相关,在这座个人意志之巅的神庙中,供奉的不仅是扬升之力,而是向各个方向四溢之力,包括了下沉。
虽然涉及了对下沉的反对,但对善恶的观点并不是罗斯科这类艺术家的工作目的所在,他们旨在还原“如其所是”的永恒系统,并臣服于超越个人意志的神秘性。对于周阳明的工作来说,偏执地以画道的方式进行了二十多年创作,是其还原系统面貌的唯一方法:一道由上而下的短道,再由下而上地重复一次,以此无限重复。这是对“一”的确认,也是对“一”的消解。周阳明的重复带来的差异,并不会将其带入偏离,因为他在用最朴素的画法,最朴素的图示来确认一个:无限从坚固中诞生,而非来自于恣意的自由。“一”是最小的数,是唯一的智者,是被认为接近无限的增长数,是无限本身。
事实上,周阳明的工作与其说是对“一”的持续修复,不如说是对“一”必须存在于系统之中的持续确认。当一存在系统之中,无限才有了启动的根基,回溯的原点,系统才能坚固不至于破碎。任何想将“一”与“无限”清晰分离或站队的企图,都是对的偏离。隐藏在一与无限的持续对抗、生成之中。唯有这种矛盾的存在,才是系统中永续动力的来源,坚固不来自于“不变”的确定性,而来自于持续对抗的确定性,正如张与驰的对抗,呼与吸的对抗,业力与修行的对抗,而这才是令生命持续以真实面貌运行,不至于偏离或堕落的唯一救赎。
3,弃绝时间
这是一张拒绝被时间施暴的绘画。
“对于刑事犯和妓女来说,时间是支离破碎的,对奴隶也是同样,这就是不幸的一个特征”。(西蒙纳. 薇依)破碎的时间是对生命的施暴,就如有人拉住你,将你带去不愿去的地方——我们的注意力在短视频结束后还未喘息,顺滑的手势就将你无缝嵌入下个视频,支离破碎的注意力,不再产生连贯一致性的沉思,当深入思考的力量变得疲软,生命就被困在另一个虚假的平滑层,这是平滑无缝的时间,也是平滑无缝的暴力:从未有一瞬的支配权真正属于你,但由于舒适而浑然不觉。事实上,我们甚至已经进化出了适应这种破碎时间的能力,生命为了适应快速切换而异化,麻木瞬间可成亢进,快感后紧接抑郁,而在这些浅表情绪之下的虚空深渊,从未被触及。
我们不愿接受当下的虚空,习惯从过去和未来中获得慰藉。但幻觉能带来救赎吗?正因丧失了真实的当下,所有的虚假填充了生命。我们并未发现,让生命痛苦的并不是当下的虚空,而是为了逃避虚空而召唤的伪装,但虚空不需要被填充,而是需要被承认,唯有直面真实才能迎来拯救。1979年的谢德庆将自己囚禁于笼子中一年。“生命是一场无期徒刑(Life is a life sentence.)”他如是说。这是一个不愿被绑架而自囚的极端分子,在窒息的绝境中,他选择了一种西西弗斯般的自由:直面痛苦的自由。这个策略涉及到了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绝望。事实上,绝望拥有非比寻常的净化功能,生命终于得以重新聚焦于本质。在周阳明2000年初的早期作品中能洞见这种深彻的绝望:弃绝了色彩、故事、情绪,以最细的笔蘸取与布面一样的色彩,“织”入布缝之间,以半年的密集工作,成就一幅空无。这是艺术家弃绝时间,直面痛苦后的自救机制,在无边无际的笔触之间,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唯有无限个专注的当下,而在这永动机之中,人通过无限次进入当下,无限次注入断念的意志,获得了自己对于生命时间的全部主权。
弃绝时间,就是弃绝目的性,弃绝憧憬与担忧,不再割裂地将生命时刻分为“好”或“坏”,无差别地专注对待每一个时刻。是的,每个当下都可能隐藏着痛苦,“Pathos”这个希腊词既表示痛苦,但也意味着转化,不妨诚实地进入痛苦,弃绝时间中的作弊通道,净化与超越,便发生了。
为什么要相信存在?
相信,并不是寻求一次性的解决方案,而是相信生命拥有超越桎梏的必然可能。这种可能不在对神秘主义的轻易交付中,也不在对金钱与权力的追逐或解构中,它存在于每个生命内在固有的无限性之中,我们需要做的,是允许生命“如其所是”地展开,以规律为路径,以热爱为驱动,以无限为指引。在物质主义征服一切的时代,作为人类精神超越桎梏的求索,艺术愈加有其必要性和不可取代的尊严。
是赤裸的,同时也是隐藏的,穿越这层遮蔽,从看见眼前的绘画开始。